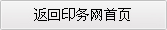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下的早期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也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绵延至今一百二十年。它源自于美国长老会,但却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经历了中国现代史上战乱变革甚至轰炸焚毁,不但未湮灭于历史长河之中,相反愈发顽强,枝繁叶茂。迄今为止,商务印书馆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乃至海外的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都设有经营机构,可谓亚洲出版界之翘楚。
史实证明,早期商务印书馆决非只在出版发行这一图书文化产业门类中影响巨大,举凡印刷、电影、唱片、画报乃至教育产业等其他当时最热门的文化产业门类,均有不凡建树,堪称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一朵奇葩。探究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文化产业史地位与学术意义,无疑是学术界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所指之早期商务印书馆,特指创立至抗战全面爆发之前的商务印书馆,在这四十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从帝制到共和的过渡,以及“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建立、北伐与抗战等历史大事,期间白话文、话剧、新诗、电影、唱片等文化产业的新事物在中国喷涌而出。与此同时,现代视听技术、印刷技术、摄影技术、广播技术纷纷相继传播入华,这一阶段是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重要的成熟期。
就商务印书馆而言,这一期间它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单一到多元,甚至从毁灭到重生的历史变迁,它不但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成熟,而且也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政治、社会在非常时期的艰辛嬗变与开拓创新,因此,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下的早期商务印书馆研究,显得重要而又迫切。但吊诡的是,关于商务印书馆研究可谓成果丰硕,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下的早期商务印书馆研究却极为不足。几乎目前所有的研究都是针对商务印书馆的某一个方面——如印刷、电影、教科书出版、画报、企业管理制度等等,而缺乏对早期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的贡献的深研。就此问题而言,目前仅有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的Gutenberg in Shanghai: Chinese Print Capitalism, 1876-1937(UBC Press,2004)和庄玉惜的《印刷的故事——中华商务的历史与传承》(香港三联书店,2010年)有一定的阐释,但总体来说,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了。笔者认为, 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视域出发,研究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地位与学术意义,不但可以给商务印书馆一个准确、客观的历史定位,而且对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也是非常重要的补充。
早期商务印书馆的文化产业活动
今日的商务印书馆,主要以图书出版、发行为主,因此不少人认为,商务印书馆是一家只与书打交道的“百年老店”,但真相并非如此。自1897年该馆创立至全面抗战爆发的1937年,早期商务印书馆确实在出版、发行、印刷等图书期刊产业中处于全国领军的地位,但不应忽略的是:它同时也在电影、唱片与玩具设计等领域里成就斐然,成为了当时文化产业领域里的多面手,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极其罕见。
商务印书馆肇始于美国基督教长老会所办“美华书馆”,鲍咸昌、鲍咸亨、夏粹芳三位“美华书馆”离职员工自主创业,遂成立了“商务印书馆”,旨在“倡明教育,开启民智”,这当然与当时戊戌变法的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不无关系。其时中国的“洋务运动”已经经历了半个世纪,但却未能真正地改变国家的命运。知识分子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了新兴先进文化与观念的介绍,此为商务印书馆创立之大背景。但需要说明的是,商务印书馆甫一创立时,梦想并不远大,首要目的无非是为了盈利而已。因此创立之初的商务印书馆主要经营两个业务。一是英文教科书的印刷出版,另一个是会计账本、教会材料的印刷,因此故命名为“商务”,即纯粹商业出版机构。
商务印书馆真正的发展,是在二十世纪。1902年,商务印书馆聘请蔡元培担任编译所长,不久后蔡元培离职,由张元济接替。可以这样说,张元济的接手,让商务印书馆进入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这也是为何当下研究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多半以张元济为中心之缘故。1903年,张元济与日本“金港堂”会社合作,吸收10万元股金,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家“中日合资企业”。合资后的商务印书馆聘请夏瑞芳担任总经理,大规模引进日本当时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并延聘了日本技师改良技术。嗣后,商务印书馆开始从事商业化图书、期刊的出版发行工作,当中既包括《伊索寓言》这样的通俗读物,也包括《最新教科书》等功能性图书,当然还包括《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都市杂志。藉此,商务印书馆一跃而成为了清季民初中国最重要的出版机构之一。
辛亥革命特别是“五四”运动之后,是视听技术转移入华、早期视听文化获得极大发展的历史节点,一大批唱片公司、电影公司相继成立。在这个过程当中,商务印书馆的身影尤其值得关注。1917年,一位美国电影人携带大量电影设备来中国,准备“大干一番”,但他抵达中国之后,竟发现“惟时华人脑筋中,犹不知电影为何物”,此人四处拜访,仍“无人过问”。不得已,他只有决定贱卖这些设备,只身回到美国。此事被商务印书馆交际科科长谢秉来知悉之后,“立电沪上总公司,备述受盘之利益”,于是以不足三千元的低价,从这位美国电影人手里买到包括“百代旧式骆驼牌摄影机一架、放光机一架、底片若干尺”[①]的成套电影器材,并成立附设于“印刷所照相部”的“影戏活动部”,此为商务印书馆投身中国电影产业之起始。杨宪益先生认为,这是“中国最早的私营电影制片机构”。[②]
这当然并非是偶然而为,一年前,商务印书馆员工鲍庆甲曾赴美考察好莱坞电影,[③]这说明了商务印书馆早已关注了当时最时兴的文化产业并希望将其移植入华。其时好莱坞电影也处于萌芽期,1911年,好莱坞第一家电影公司内斯特电影公司才宣告成立,而当时的好莱坞,不过是一个固定人口不足一万人的小镇而已,而电影产业当时也只是刚刚出世的新兴产业。商务印书馆视角之敏锐,由此可见一斑。
商务印书馆成立“影戏活动部”之后,拍摄了中国最早的两部故事电影《阎瑞生》与《红粉骷髅》,它们都是情节跌宕起伏的侦探电影,前者由中国导演先驱任彭年执导,而后者又由袁世凯的儿子袁寒云与该片导演管海峰担任编剧,这与当时侦探小说在中国的走红密不可分,当然当中也夹杂了当时美国的侦探片元素。这两部电影上映之后,社会褒贬不一,肯定者评价:“国人自摄影片,竟能臻此境界,殊出意料之外”,[④]可见其技术水平在当时已居于先进地位。此后,商务印书馆还邀请梅兰芳担任导演与编剧,推出了《春香闹学》与《天女散花》两部戏曲电影,此为中国戏曲电影的渊薮。1926年,商务印书馆收购了国光电影公司。尽管商务印书馆提出“以教育时事风景为限”作为从事电影活动的宗旨,但却在中国早期电影产业实践中取得了卓异的成就,这是不争的事实。
电影如是,唱片业亦不例外。与摄影技术一样,录音技术移植入华,几乎与国外同步,[⑤]因此商务印书馆进入唱片业也较早,在亚洲范围内亦算先驱之一。1922年,主要推行此工作的是学者赵元任。当时他应商务印书馆之邀,为商务印书馆灌制六张国语教学的唱片,用于电化教育之用,此为商务印书馆涉足唱片业之起始。当时这些唱片主要卖给国语不好的华侨,可谓是“对外汉语教学”之滥觞,据当事人回忆,商务印书馆开发的这一套唱片销路奇佳,一度卖到仰光。[⑥]需要说明的是,早期商务印书馆在唱片产业领域的成就,主要在电化教育层面,即推出语言学习等类别的唱片。当时中国的唱片业,本身就是一个分众传播的市场,电化教育唱片、戏曲唱片与流行音乐唱片三足鼎立,而早期商务印书馆当仁不让是电化教育唱片业的领军企业。除了赵元任录制的国语教学唱片之外,早期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一些科普常识类的介绍唱片,并利用自己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拍摄了《幼儿园》、《养蚕》等科普电影,既践行了“以教育时事风景为限”这一宗旨,也很快地在电化教育产业领域奠定了重要的地位。
而且在文化产业诸领域中,早期商务印书馆还是中国现代玩具业的先驱。在晚清以来的上海,玩具市场长期由外商把持。张元济在日本考察玩具市场之后,认为玩具是儿童启蒙的重要工具,必须要由中国人自己设计生产。刚投入生产时,尽管“自制教育玩具出品尚佳,与西货不相上下,唯成本较贵,定价未能过廉”,[⑦]但“玩具房制造儿童教育用品及有益儿童身心之各种玩具去年出品甚多,陈列店堂,大受顾客欢迎”,[⑧]并且生产规模不断扩张,“又自制儿童教育品及各种玩具已达二百三十七种,比上年加增六十二种。”[⑨]
此外,早期商务印书馆还是中国教育文化产业的先驱,先后开设了商业补习学校、小学师范讲习所与国语师范学校等教育培训机构近十所。以“商业补习学校”为例,其创立之由是“为本馆输送编辑、出版、印刷、发行的专业人员”,[⑩]1909-1923年,商务印书馆连续办了七届“商业补习学校”培训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商务印书馆的人才之缺,但显然商务印书馆不可能将这些学员照单全收,譬如杭穉英、郑曼陀等当时首屈一指的商业画家都是该校毕业生,因此“商业补习学校”仍是一所商业性质的教育产业机构,这确也构成了商务印书馆在教育文化产业上“为时代之先”的历史地位。
文化产业离不开文化企业,更离不开现代企业制度对文化生产、传播的促进。在这个层面上,商务印书馆的现代企业制度也开时代之先河,史实证明了它是中国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文化企业,这也是商务印书馆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所作出的贡献。在商务印书馆成立之时,中国虽然有名义上的文化企业,但它们几乎都缺乏正规的建制化,更遑论现代企业制度。但商务印书馆却一开始就处于一个制度化的背景之下,这尤其难得。商务印书馆成立不久,便与日商合资,并积极引入对方技术,这可以看作商务印书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之起始。嗣后,商务印书馆在经营上采用总经理负责制,聘请专业人士专职从事出版、电影、幻灯片与唱片等产业活动,建构了“股东大会-董事会-总务处”的管理模式,可谓权责分明。而且商务印书馆有非常强烈的版权意识,早在1918年,张元济赴日谈引进影片时,就曾称“余意首要得人,次须取得版权”、并且希望,“与日方合资,可得人才、可得版权”。[11]及至新文化运动之后,商务印书馆更是在全国设立分号、发行所,并且在全国出版行业率先建立、健全了印刷、仓库与发行的章程以及图书质量检测制度。[12]不难看出,商务印书馆在管理制度、股份制度、分支机构设立与市场经营上具备了一个现代企业的特征。
需要说明的是,现代企业制度是商务印书馆得以在战火中凤凰涅槃的重要因素。1932年淞沪战事爆发,上海地区大量出版社、报馆因为战争的爆发而破产,而商务印书馆又成为了日军重点的迫害对象。1932年1月28日,日军进犯闸北,商务印书馆惨遭轰炸,尔后又被日本浪人纵火。张元济之子曾回忆在这场劫难中“商务在闸北的印刷厂和东方图书馆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毁。图书馆所藏之书全部化为灰烬。那天正吹东北风,纸灰由闸北直吹到沪西,落在我家园中”。[13]但时任总经理王云五当机立断,与董事会一道按照规章制度作出紧急决策。一方面“上海总馆、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所、发行所、研究所、虹口西门两分店一律停业;所有总馆同人全体停职;总经理王云五、经理李拔可、夏鹏辞职照准。”另一方面决定“公司以后方针俟立集股东会议决定。组成特别委员会,办理善后。”[14]正因为有完善的企业制度作依托,使得商务印书馆可以迅速在灾后奇迹般地复业,并且再度成为国内文化产业领域的领军企业。
如上是商务印书馆除却书刊印刷、出版与发行之外,在其他文化产业领域里所作出的成就。早期商务印书馆在出版领域的卓著贡献可谓众人皆知,如1929年至1937年编辑出版的《万有文库》(共计1721种、4000册)、1902年至193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教科书多达390多种等等,[15]至于各类畅销书则不胜枚举,本文兹不赘言。从前文所论可知,早期商务印书馆决非简单的出版机构,而是一个多元业态、多样经营的文化企业,这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上并不多见。因此,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视域来探究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历史定位问题,显然有一定学术意义。
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出现: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发展必然
要探究早期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视域下的历史定位问题,则必须简要回顾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早期发展阶段。由在华外侨移植入华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与中国的近代史一同发轫,肇始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上海开埠时期。在嗣后的半个世纪中,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可谓艰辛开拓,从《北华捷报》、“A.D.C剧团”与“吉庆公所”等新生产物艰难起步,依靠“西俗东渐”与中国社会、文化现代化的浪潮逐渐自我完善,从单一门类向多元经营逐步转型。[16]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逐渐从萌芽期向成熟期过渡。
藉此笔者认为,商务印书馆的出现并非是“横空出世”,而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发展必然,理由有三。
首先,二十世纪以降,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已较为成熟、发展较为完备,出现了“多元业态”的机构(或都市空间),早期商务印书馆是个中代表。
在十九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萌芽期,文化产业体系并不完备。无论是乐队、报刊、剧院还是影楼、演出中介与书画市场,其最大的特征是经营业务上的单一性。但到了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业态开始逐步走向多元化,当中另一个重要的代表就是上海的张园。作为当时沪上最重要的文化产业中心,张园不但承担张贴广告、展览拍卖与演讲聚会的场地租赁业务,而且还有西餐厅、弹子室、抛球房、茶楼、电影院、影楼与中西餐厅等附属文化产业,是为中国最早的“文化产业多功能综合体”。早期商务印书馆不但与张园处于同一历史时期,而且与张园有着相似之处,都属于多元业态的文化产业。一方面,这显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逐步走向成熟,另一方面也证明了,早期商务印书馆本身是时代的产物,是变革期中国社会应运而生的结果。
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多元业态”,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在“西俗东渐”语境下的对于世界的回应。当时在欧洲、美国与日本,因为视听技术、印刷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视听、图书文化产业,其发展可谓是如日中天。因为世界殖民战争而被迫卷入全球化浪潮的中国,自然也会因为大量在华外侨的存在而对这些新兴的文化产业产生兴趣。而本身视野较为开阔的商务印书馆对于这股“西风”采取了积极的回应态度,这也是早期商务印书馆走向“多元业态”的重要动因。
现在看来,尽管早期商务印书馆涉足电影、唱片等新兴文化产业形态并不成熟,但是这种理念与方式却在当时自有其先进性。文化产业不同门类本身具备共生性,从媒介的角度看,文化产业具备同内容、跨媒介的共生性。[17]譬如商务印书馆在推出国语学习唱片的同时,还推出了纸质教材,而商务印书馆每推出一些科普电影,则亦在同时推出一些与之有关的图书。这一方面会给相关文化产品带来成倍的销量与影响力,另一方面会平均不同行业部门的利润,在获利上不但“预备特别公积,以资调剂”,而且“有时或有特别推广营业及填补意外亏耗之用”,[18]这种灵活的多样化经营促进早期商务印书馆文化产业体系的日趋壮大,也带动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体系化、规模化的发展。
其次,早期商务印书馆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审美档次与整体格调产生了质的变化,促使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进入到了“现代性”的维度当中,进而逐步告别了普遍“下里巴人”的时代。
仔细来看,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在萌芽期,先后经历了两批受众。一批是移民来华的早期在华外侨,他们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发生的推手,以工部局乐队、A.D.C剧团、《北华捷报》与美华书馆等等为个中代表。[19]随着都市开埠的增加、中国卷入全球化浪潮的加深,一批中国本土的受众随之逐渐出现,当中既有买办大班、新式学生,也有归国华侨、城市平民等等,当然还有大量的“外来打工人群”。[20]因此,绝大多数人并不具备消费上述舶来文化产业的水准与能力,因此,另一些属于中国人的文化产业业态随之出现。当中既包括“千篇一律,都离不开秽亵二字”[21]的小报,以及《姊妹花》《苏州老骚》等“销路极畅”的艳情小说,也包括沪上各路妓院、低档新式酒楼(以及戏园)等冶游娱乐场所。不难看出,上述诸文化产业活脱脱地勾勒出了一个格调不高、内容低俗的“虚拟/现实”都市文化空间。
就萌芽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而言,如果抛却在华外侨所兴办的文化产业,那么当时的中国文化产业显然在审美档次与整体格调上呈现出了“下里巴人”之风。究其原因,一方面,当时可以消费现代文化产业的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属于真正的“有钱有闲”阶层,最多只是在开埠环境下“附庸风雅”而已,难以说他们真的认识到新兴文化产业所带来的新思想、新文化与新观念,更奢谈将这种“新”的意识形态产业化,但对于新式生产、传播方式之下的低俗文化,却青眼有加;另一方面,当时中国处于帝制时代晚期,即王德威所言之“被压抑的现代性”,其时民众有现代性的诉求,文艺创作者们也对“无中生有的都会奇观”与“近代西方文明交错影响”有着特殊的“现代性”体会。[22]但他们不可能无拘无束地表达现代性的意识形态诉求。因此,当时中国文化虽看似呈现出了面向现代性维度的转移,但受制于社会制度的与传统观念双重束缚,现代性即使有可能萌芽,亦会处于一种“被压抑”的状态之下。嗣后的辛亥革命打碎了压抑文化朝向现代性发展的政治桎梏,这是中国现代文化得以在合适的土壤内迅速发展的外在动因。
商务印书馆的出现,显然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中的中流砥柱,可以说它在现代性这个意识形态的生产、传播中居于一种先锋且扛鼎的地位。这既与其出现的历史时期密不可分,也反映了商务印书馆的主要负责人审时度势、把握时机的过人之处。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商务印书馆虽然出版过一些畅销书,也兴办过一些市场化的期刊,也拍摄了一些情节化的电影。但这些文化产品却在总体上仍与晚清小报、艳情小说有着本质的区别,他们在意识形态总趋势上是与辛亥革命的大势相一致的。
据不完全统计,在1910-20年代的廿年间,商务印书馆总共出版各类图书400种,拍摄电影10余部,出版唱片40余种,出版杂志10余种,制作玩具更不计其数。在1919年,商务印书馆年营业额“合计洋三百一十五万一千三百五十八元二角四分四厘”,[23]其产品的发行量之巨大、影响之广泛可想而知。因此,早期商务印书馆在相当程度上提升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审美档次与整体格调,并已然成为了现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主要的推陈出新者与建设者。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一个大背景,那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民族企业的迅速发展,这与国际银价的变化、战争的刺激以及中国的都市化、工业化进程有着复杂的联系。[24]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显然与这个大背景休戚相关。文化产业本身也是国民经济产业的一种,尤其在辛亥革命之后,“实业救国”、“振兴国货”成为国家建设主旋律,政府也相继出台了《奖励国货办法》等章程条例推动民族经济发展,[25]早期商务印书馆在文化产业领域内所获得的成功,当然也与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
第三,早期商务印书馆见证了以市民文化为基础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崛起,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反映了当时中国都市社会的形成与新兴阶级的壮大,它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得以迅速发展打下了社会基础。
文化产业,英文是cultural industries,即工业化的文化生产。其能指包括了现代性语境下的工业文明,因此显然是资产阶级制度建立与工业革命之后的产物。古希腊的城邦时代与中国的唐宋时期,尽管有文化消费,但并不构成产业。因为对产业属性的评判更多是倾向于对生产而非消费环节,其要素包含新兴阶级的生产关系与先进的生产力。[26]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也不例外,萌芽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处于中国市民阶层的形成期,一方面既要满足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总体需求,另一方面还要承担起时代启蒙、推动社会市民化发展的历史重任。
商务印书馆成立之时,中国已经被迫卷入全球化长达半个世纪,期间不但出现了新兴工人阶级,也孕育出了市民阶层。1900年,上海地区人口超过100万,大多数是新近涌入上海的外来移民,他们当中大部分人都成为了上海的新兴市民阶层,1910年上海500人以上大厂共有职工7.7万人,其中在外资工厂中的工人为3.5万人,[27]如果算上学堂学生、报馆报人、洋行伙计等等,总人数预计在20万左右。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显然足以构成市民阶层这一新兴社会群体。商务印书馆的出现,无疑与其形成不无关系。无论是巴黎、伦敦、布鲁塞尔还是上海,但凡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是市民阶级推动使然,成熟的现代文化产业,其核心都是市民文化。商务印书馆在当时所推出的《东方杂志》、“万有文库”以及各种教育片、故事片,从受众对象上看,都是处于培育期的市民阶层,早期商务印书馆顺应时代潮流,在培育市民阶层上付出甚多。
从早期商务印书馆所推出的产品不难看出,自成立伊始,商务印书馆就矢志不移地推行“以扶助教育为己任”[28]的宗旨,张元济自己也认为:“国民教育之旨,即是尽人皆学,所学亦无需高深,但求能知处今世界不可不知之事,即可立于地球之上”。[29]与当时绝大多数书商、报馆不同,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国民市民化”的启蒙重任,而正处于辛亥革命与“新文化运动”变革之中的民众,恰也有这种启蒙的文化愿望与精神诉求。
由是可知,商务印书馆的出现、发展本身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发展必然,是市民阶层及市民文化形成的结果,它与张园的出现一样,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逐步从萌芽期走向了成熟。
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现代文化产业史地位
早期商务印书馆,虽然起步于上海这个繁华的十里洋场,但却历经磨难,甚至遭受日寇的轰炸,可谓中国现代文化产业浴火重生、凤凰涅槃的真实写照,其发展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可谓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缩影。因此,给早期商务印书馆赋予一个准确的文化产业史定位,颇有必要。
首先,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早期商务印书馆是推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走向成熟的先行者。
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从萌芽期到成熟期,是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是内容与形式的双向成熟。萌芽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其内容难以称之为“现代性”。前文已经提到,在华外侨兴办的乐队、英文报纸,虽然在内容上颇为新颖,但却针对在华外侨,与中国现代文化关系不大;但当时中国人自己兴办的文化产业,虽然在生产、传播的方式上与古代文化生产消费相比有本质差异,诞生了官书局、“吉庆公所”与各类小报等新兴文化产业业态,但内容以奇谭怪事、艳情小说、传统戏曲与四书五经为主。并且从形式上看,萌芽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在业态上也颇为单一,主要是出版产业,不同的业态而且也缺少融合性。
进入二十世纪以来,视听技术传播入华并获得较大发展,以及新的文化形态如话剧、白话文、新诗等相继出现,特别是辛亥革命的爆发,使得中国人在观念上获得了解放,由清政府主导的各类报案、文字狱成为历史,亦这促使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从内容到形式上产生了变革,这也给商务印书馆以极大的发展机遇。但是商务印书馆在辛亥革命爆发之前,已经在影响力、技术等层面上有着数十年之久的耕耘积累。一方面也在出版领域努力较多,尤其在出版教科书、词典方面,积累了丰厚的出版经验与读者群,而且商务印书馆本身源自于“美华书馆”这个在华历史悠久、具备现代文化产业属性的出版机构,与当时许多“官书局”或民营出版机构相比,商务印书馆拥有较为先进的管理方式与眼界,因此在管理、技术上都先人一筹;另一方面就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注重技术革新,张元济甫一接手商务印书馆,第一步就是引进日本的资本与先进印刷技术,使其成为在技术上首屈一指的企业。当然这也与商务印书馆处于上海这个中国最为开放的城市密不可分,其时上海不但拥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与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而且商务印书馆一直在租界办理编辑、发行业务,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当时纷乱政治时局的干扰。[30]因此,一俟进入到特定的历史时期,它自然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从萌芽走向成熟的先行者。
正如前文所述,早期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上创下了许多个“第一”,当中既有形式上的创建,也有内容上的革新。历史地看,这当然是在受众、技术上长期积累、厚积薄发的结果,因此得以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成熟期之初大有作为,并且在技术、观念、管理方式上影响到了同时代其他的文化企业。譬如商务印书馆《最新教科书》的出版,这既给商务印书馆带来了巨大利润,也为提升国民素质、促进市民化进程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就在《最新教科书》出版后不久,陆费逵便成立中华书局,并在《中华书局宣言》称:“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31]欲与商务印书馆一争高下。及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连一些出版畅销小说的新出版社如北新书局、世界书局、开明书店、大东书局等等都瞄准教科书市场,[32]这不得不说是商务印书馆所奠定的影响基础;此外还有科普电影,商务印书馆以“教育电影”之名打开科普电影的市场,引起社会极大反响。1932年,数十位知名学者发起成立“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由蔡元培任主席,四年后,该会陈友松、卢时白两位理事在上海合办了一个中国电影教育用品公司,并出版了《电化教育》周刊,[33]自此之后,中国的科普电影产业走上了发展的额快车道,以孙明经为代表的科普电影导演、制片人将科普电影与国家建设、公民教育与电影产业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促使科普电影的设备生产、拍摄推广成为当时中国电影产业中重要的组成。凡此种种皆证明了,早期商务印书馆是推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走向成熟的先行者。
其次,早期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中有着承上启下、推陈出新的历史价值,它是现代文化产业“中国化”发展的推动者、见证者。商务印书馆的成功证明了,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必须要与时代、国情相适应。因此,一部早期商务印书馆发展史,也是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中国化”的进程史。
在中国现代文化企业中,如商务印书馆这般多样化经营且持续营业百余年的,并不多见。纵观早期商务印书馆的历史。不难发现,因为晚清的时局造就,使其被打上了特殊的历史烙印。它源于美国传教士兴办的“美华书馆”,创立之初并与日商合资且引进日本技术。这是现代文化产业在近代中国不得已被打上的“舶来性”烙印,但早期商务印书馆经历了四十年的发展也证明了它不断在发展中适应中国国情,推动现代文化产业的“中国化”发展的特性。这里所言之“中国化”,是针对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特殊属性而言的。作为“西俗东渐”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在相当层面上具备“舶来”的特征,无论是内容、技术还是形式,源自于中国本土的并不多,其发生也是在华外侨“移植”的结果,因此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发展,必须要符合中国国情、满足中国的时代需求,离不开“中国化”这一基本原则。藉此本文认为,商务印书馆推动现代文化产业“中国化”在于两个方面:一是内涵的中国化,另一个则是路向的中国化。
先说内涵的中国化,文化产业的核心是文化,中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很强的“载道”传统,即文化要有时代性,优秀的文化产业当然更要在大时代中有所作为。早期商务印书馆四十年发展史,可以说正处于中国历史上的大变局。商务印书馆所从事的文化产业活动以及所推出的文化产品,皆应大势所趋,反映了时代的迫切需要,这显然与其他萌芽期的文化产品有着本质差异。在国难当头的十九世纪,相继签订的《马关条约》、《辛丑条约》堪称丧权辱国,而与之共生的“庚子国变”、甲午战争更是将中国推向了亡国灭种边缘。但当时在中国影响最广泛的文化产品竟然是各种“谈女人,谈性交,红情老七,雪艳老八,可实在是无聊得可以的事情,不但无聊,而且近于下流”[34]的低俗小报与一些忠君尽孝、才子佳人戏曲演出,它们皆以“不谈国事”为共性。这当然与晚清严苛的言论管制不无关系,但毋庸讳言,当时中国文化产业的大部分从业者,既缺乏时代感,也谈不上有什么责任心,这使得萌芽期的中国现代文化产业诸多内容在内涵上严重与时代脱榫。
商务印书馆虽然挂名“商务”,但却与时代、国事休戚相关。早在科举制尚未废除的1903年,清政府刚刚颁布学堂章程,商务印书馆就按照“学期制”编辑出版了我国第一套初等小学教科书即《最新教科书》,而当时沪上许多出版商正在图眼前之利,大肆推出各种艳情、黑幕小说与低俗小报,但事实证明,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获得了巨大成功,引领一时风尚,但格调低俗的出版商们均在“五四”前后被社会逐渐淘汰。至于在“五四”运动之后商务印书馆推出“教育电影”、编辑出版“万有文库”,更是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建设期瞄准时代需求、符合国情需要的“载道”之举,这不但使商务印书馆获得了利润、扩大了规模与影响力,而且使自己独立于时代的潮头之上,引得当时一批文化产业企业纷纷效仿。
其次则是路向的中国化。这里所言之路向,主要是指商务印书馆的生存、发展形式。任何一个企业,要想在中国获得好的发展,则势必要对中国的消费者有所了解,文化企业当然也不例外。商务印书馆之所以能够绵延百余年发展不衰,并在战火纷飞之中顽强坚挺,当中很重要一个原因就在于,商务印书馆在生存、发展的过程当中一直坚持“中国化”的路向,对于中国的国情有着充分的认识,[35]张元济对此一直持明确观点,他“认为国外先进事物应该效法,但必须适合国情”,特别“编写教科书既要适合国情,又应适应时代的需要;不可抄袭科举时代的传统书本,也不可笼统翻译洋课本”。[36]
早期商务印书馆处于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半封建中国,当时中国的文盲数量巨大,而且贫困人口庞大,而且又有着几千年的宗法封建传统与农耕文明,意识形态的现代化之路艰辛无比。这一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必然有着自己的特殊性,而不能将伦敦、巴黎或纽约的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照搬照抄。早期商务印书馆在推出文化产品的过程中,非常注重与具体国情的结合。据沈百英回忆,当时编撰教科书时,张元济曾再三强调,“首先从事教材、教法的改革,编出整套合于国情的教养员用书。”[37]1930年代在编撰出版“大学丛书”时,序言中再度声明“惟我国学术幼稚,尚无此项专书,而外国书籍又不尽适于国情,学者苦之。”[38]而商务印书馆在进行玩具的设计、生厂上,更是注重对国情的把握,一方面,借助当时最时尚的铁皮、塑料材质,另一方面,将中国传统玩具如五子棋、象棋、滚铁圈等与之结合,制作出中国孩童特别是家长普遍喜爱的铁皮跳鸡、塑料象棋等新式玩具。而且,注重国情还体现在商务印书馆的薪酬制度、管理方式上,商务印书馆虽然采取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但早期商务印书馆处于民族工业的上升期与工人阶级的形成期,商务印书馆作为资方,认识到日益壮大工人阶级不但是市民阶层的重要组成,而且必然会成为日后中国社会的主要力量,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国情之一。因此,早期商务印书馆的管理者对工人阶级的诉求有着一定的尊重与认识,譬如张元济曾以“互助合作、同存共利”作为其劳资关系的指导思想,并在商务印书馆推行福利保险制度。1931年,时任总经理王云五准备推行“科学管理法”,此事已经在董事会上获得了通过,但遭到了工会的一致否定,王云五只好将其改为“部分推行”,[39]上述对于工人阶级的清醒认识在当时上海其他企业如纱厂、面粉厂中是难以做到的。正因此,早期商务印书馆也成为了当时左翼文艺运动的主要阵地,并为左翼文艺的发展提供了温润的发展土壤,[40]沈雁冰、周扬、周立波等共和国文艺、财经领导人都曾来自于商务印书馆。
综上所述,早期商务印书馆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不同门类如出版、电影、唱片、玩具、教育产业乃至现代文化企业制度建设中都有卓著的贡献,开辟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多个“第一”。它有力地建构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多元业态共生的局面,改变了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总体格调,从而推动了市民文化的形成,反映了市民阶层的文化需求。因此,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视域看,早期商务印书馆不但是推动中国现代文化产业从萌芽走向成熟的先行者,而且它还是现代文化产业“中国化”发展的推动者、见证者,有力地证明了文化产业只有与中国国情相适应才有发展前景的这一历史事实。
注释
[①] 徐耻痕:《中国影戏之溯原》,中国电影资料馆编:《中国无声电影》,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6年,1327页。
[②] 杨宪益:《去日苦多》,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91页。
[③] 谷剑尘:《中国电影发达史》,中国教育电影协会编:《中国电影年鉴》,1934年。
[④] 严芙荪:《我之“阎戏”谈》,《申报》,1921年7月26日。
[⑤] 韩晗:《早期视听文化: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起源》,《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⑥] 陈尘若:《赵元任和商务印书馆》,蔡元培、蒋维乔、庄俞:《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604页。
[⑦] 张元济:《在民国九年商务印书馆股东常会上的报告(1920年5月8日)》,张元济:《张元济论出版》,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2页。
[⑧] 张元济:《在民国七年商务印书馆股东常会上的报告(1918年4月13日)》,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4卷·诗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38页。
[⑨] 张元济:《在民国九年商务印书馆股东常会上的报告(1920年5月8日)》,张元济:《张元济论出版》,张人凤,宋丽荣选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2页。
[⑩] 赵而昌:《商务印书馆为我国文化事业输送人才》, 顾国华编:《文坛杂忆·全编·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5年,第19页。
[11] 张元济:《张元济日记》,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42-349页。
[12] 相关研究可参阅何国梅《商务印书馆的现代企业制度研究(1897-1949)》(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及潘文年《20世纪前半期的商务印书馆给我国现代出版企业的启示》(《出版科学》,2007年第12期)。
[13] 张树年:《我与商务印书馆》,蔡元培、蒋维乔、庄俞:《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90页。
[14] 上海市新闻出版局,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编写组编:《上海商务印书馆职工运动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91-92页。
[15] 庄俞:《谈谈我馆编辑教科书的变迁》,蔡元培、蒋维乔、庄俞:《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604页。
[16] 韩晗:《略论中国现代文化产业史的分期问题》,《东方论坛》,2016年第6期。
[17] Marsha Kinder:Transmedia Frictions: The Digital, the Arts, and the Humaniti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4, p.151.
[18] 张元济:《在民国七年商务印书馆股东常会上的报告(1918年4月13日)》,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4卷·诗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41页。
[19] 韩晗:《在华外侨与中国现代文化产业的发生》,《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4期。
[20] 此处所言“外来打工人群”是指十九世纪后半叶陆续从郊县涌入开埠城市的失地农民、渔民等剩余劳动力,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现代经济逐步瓦解了中国的农耕经济,导致农产品价格暴跌,又因为经年累月的海战(晚清绝大多数中外战争都是海上战争,包括黄海的中日甲午战争、渤海的中日刘公岛-威海卫战役、珠江口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东海的中法马尾海战、北部湾的中法镇南关之战等等,因此清政府对于西方列强的恐惧多在“船坚炮利”层面),这使得大量渔民不敢出海。珠三角、长三角大量农民、渔民不得不涌入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求生,当中不少人成为了杜月笙、周至元等工商业巨子,有的被雇佣为工厂的底层工人或店铺伙计,有的靠经营餐馆、炒货店为生,他们属于“前市民”阶层的特殊阶层。
[21] 二云:《小报论》,《铁报》,1930年5月13日。
[22] Dewei Wang:Fin de Siècle Splendor: 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9-1911,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340-341
[23] 张元济:《在民国六年商务印书馆股东常会上的报告(1917年5月19日)》,张元济:《张元济全集·第4卷·诗文》,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325页。
[24] Marie Claire Bergere. “Golden Age of Chinese Capitalism”, John King Fairbank & Denis Crispin Twitchet eds.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Republican China 1912-1949, Part 1,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751.
[25] 施则臣编:《新编实业法令》(上编),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第195-197页。
[26] [美]威廉·I.鲁宾逊,高明秀译:《全球资本主义论:跨国世界中的生产、阶级与国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70-71页。
[27] 丁日初主编:《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二卷(1895-1927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495页。
[28] 张庆:《张元济先生年表》,张树年:《张元济论出版》,北京:东方出版社,2015年,第274页。
[29] 张树年:《张元济年谱》,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38页。
[30] 当时商务印书馆的法律诉讼都由租界方解决,譬如美商米林公司曾控告商务印书馆印行《英汉双解韦氏大学字典》侵犯版权,此案系由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判决的。
[31] 钱炳寰:《中华书局大事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页。
[32] 石鸥、吴小鸥:《简明中国教科书史》,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第103页。
[33] 同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了电影教育委员会和播音教育委员会,这是我国最早的政府电教机构,两个月后,无锡江苏教育学院开办了电影播音教育专修科,这成为我国最早的电教专业。详见毛毅静:《影像记忆:百年变迁的教育叙述》(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5年)。
[34] 王忆真:《谈小报》,铁报,1936年7月26日。
[35] 南开大学政治学会:《天津租界及特区》,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页。
[36] 张树年:《我与商务印书馆》,蔡元培、蒋维乔、庄俞:《1897-1987商务印书馆九十年:我和商务印书馆》,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289-290页。
[37] 沈百英:《我与商务印书馆》,同上,第287页。
[38] “大学丛书”(序言),金善宝:《大学丛书·实用小麦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1页。
[39] 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9页。
[40] 韩晗:《论现代印刷业与1920年代的左翼文艺》,《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